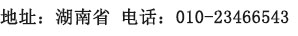星期天的下午,百无聊赖,独自坐在店内,思绪万千,我沏上一杯热茶,凝望着书店外柳树上的青枝绿叶。忽然一声:“磨---剪子唻--------锵---菜----刀-------”的叫卖声,便勾起了我久远了、并熟悉的回忆。啊!还挺标准的叫卖声,久违了!叫卖人一定是一个老者吧?
我年少的时候,改革开放不久,庙湾的商业网点不是象现在这样“普及”和“发达”,家的周围(就是大路边,或者叫街上)也有几家小铺,都是卖些油盐酱醋、火柴肥皂或开水之类的,虽然也挺方便,但还是不如那些送到家门口的。家里缺了点什么,大人就说:“听着点,一会儿就该来了”。
果然一会儿就会听到外面的叫卖声。那时候,走街窜巷叫卖的随处可见,凡是家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,或需要修修补补的什么都有。象卖菜的、卖香油,酱油的、卖针头线脑的、锔锅锔碗的、剃头刮脸的、旧鞋换碗的、修笼屉、卖野菜、收废品的等等。
————“糖葫芦,糖葫芦,又甜又酸的糖葫芦。”“收…破烂儿,收…破烂儿,破烂换钱…”“换大米、换小米儿、换方便面!”“卖小鸡来…好小鸡哟…”“收头发辫子,收鸡毛、Ba子毛(鸭子毛)了…”“油条、面呱嗒儿啦…”“换瓢,新瓜新瓢呱呱叫,一个只要块八毛…”叫卖的声调也是各有特色、此起彼伏的,而且还各持有能敲打出声响的“家伙式”。在家里就能听到远远的敲打声和叫卖声,就知道干什么的来了。有时候,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还会追着他们,学着他们的叫卖声。如果把菜刀或剪子拿出去磨,不用在外面守着,只要外面再喊起:“磨---剪子唻------锵---菜---刀-------”就是告诉你已经磨好了。现在磨一把菜刀需要五元钱,那时是一角钱。
早春时节,乍暖还寒,庙湾街里不时有一些身穿黑布对襟的乡下人来做一种“赊小鸡”的生意。这可是一个现如今绝对见不到的行当了。
赊小鸡的汉子大多来自山东的,他们挑着两只直径足有5尺长的浅筐子。筐子上面蒙着黑布,一个筐子里放养着六、七十只刚孵出的鸡崽。他们一进院子就放开嗓门高声地喊起来:“赊--------小鸡---来------”
至今,我还清楚地能记起那满箩筐毛茸茸的小鸡,一起乱哄哄地拥挤着,一起叽叽喳喳叫着的神气。那卖小鸡的汉子不时从大口的瓶子里,抓一把泡好的湿漉漉的小米撒进箩筐里,于是就又一次在鸡群里掀起一波拥挤的热潮------赊小鸡的摊子是最有人气的买卖,不用交现钱,只需要在赊小鸡贩子的本子上记个帐,到了秋后,山东汉子才来收钱。
平淡如水的日子一天一天流逝着,不觉中,路边的老槐树过了开花的日子,天慢慢变得热了起来。街上树荫下,又传来冰糕的叫卖声了。时至今日,我依然这样坚定的认为:天底下叫卖冰棍的声音恐怕找不出比叫卖声更好听的了。卖冰糕的人骑着自行车,驼着冰糕箱满大街跑,边跑边喊:“卖冰糕------冰糕、冰糕,三分五分地------------卖冰糕------冰糕、冰糕、三分、五分地------”那悠长、悠远的音调完全可以谱成曲子传唱的,那音那调多少年来一成不变,就那么不紧不慢,韵味十足的在我们这里的夏日荡漾着,一曲唱罢余音袅袅------那美妙、独特、韵味十足的冰棍叫卖声啊,估计五十岁以下的农村人是都能回忆起来的。
农村里的叫卖声说起来也是有些规律的。按照节气、按照时间而各不相同。
在南腔北调的叫卖、吆喝声里,最难忘的是一个瞎眼老人的声音。那老人是算卦的,现在想想,当年他也就是五十开外的年纪,穿一身油汁麻化的呢子中山服,衣服上搭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布夹子,用拿一根长长的竹竿,戳戳点点的走------至今,我奇怪那个整天顶风冒雨奔波在外的老人怎么就晒不黑呢,老人那国字型的脸上最显眼的是那黑黑的落腮胡子。老人一边拖拖塌塌地走,一边用短促的嗓音字正腔圆,一字一顿地喊着:“摇卦------抽------书------”
上高中的时候,罗庄附近有个卖豆腐的老头,他的叫卖声堪称一绝:大老远就能听见猛地一喊:“豆腐!”声音短而有力,让你冷不防吓一跳,据说有个老太太当场被吓得医院。前些年还能听见这独特的叫卖声,这几年已听不到,或许是上了年纪吧!
时光是一把利剑,把过去的岁月剪成了碎片。可当它散落一地的时候,又突然重新胶合在一起,拼成了人们完整的记忆。记忆就像抽屉一样,隔一段时间,人们就想去打开它们,从里面随便拿出一样,即使不经意的一声叫卖,也可以奇迹般在眼前复活。
有时我会思考:人,是否就是喜欢怀旧?是否只有潜入记忆的深海,才能打捞到瑰丽的珍宝?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,正在普遍的物化和滥用,变得非功利不可取。那时候的叫卖者,无法领教现在高音喇叭的威力,否则,他们不会费心劳神的琢磨文字的组合和声音的奇妙组合。只需对准话筒,卖啥吆喝啥。电视里,男方黑芝麻糊的广告,已经是久违了,不知道那个叫卖的女人,如果没有改行,是不是一如往昔的叫卖:“买芝麻糊哎------”好让人们在她悠扬的长歌里,还会允吸到一丝浓香,一缕温情?
如今,这样的叫卖声越来越少,在市声喧嚣的时代,真正的叫卖声正渐渐淡出,趋向寂静。若再想听那嘹亮悠扬,或低回婉转,或沙哑短促的叫卖声,恐怕只有在回忆里了!
久远的叫卖声,以它浑厚,坚实,温润的磁性,将上一个世纪的名间生活以最生动,最形象,最具体,最鲜活的形式记录下来,一直好多年后,我仍然期待去解读他们------
可惜啊,随着社会的进步,这些民间的“艺术”随之失传了,在一些城市的庙会上象表演似的叫卖,或搬到舞台上作为艺术的表演,却怎么也感觉不出过去原有的味道。象现在偶尔的“磨剪子磨刀的”、“修理纱窗的”的叫卖,也大都相差更远,没有了过去的韵味了。
平淡如水的日子里,时常想起那些离开我们已经挺久远的往事。每当想起那些往事的时候,那些曾深深印在我们这代人心灵深处的叫卖、吆喝声也时常又在我的耳边回响起来了......
(来源:微合峪编辑:扫地僧)
将城市装进口袋,点击“阅读原文”下载栾川在线APP!
↓↓↓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